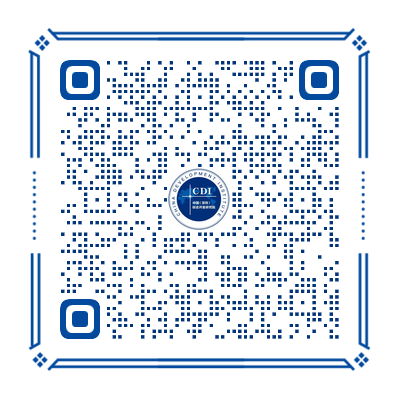第139期银湖沙龙:《全球气候治理与增长方式和发展路径创新——中国气候变化国家学说的自信》
时间:2017-05-14 14:49
主讲嘉宾:邹骥老师
主 持 人:李津逵
[实录内容]
李津逵:今天是一个小规模、高规格的沙龙。
邹骥教授坐在这儿我特别自豪,自豪在于这位参加整个气侯谈判的专家是我的同学,我就觉得非常自豪。我更加自豪的是,他现在是深圳人,这要归功于深圳哈工大等等领导,代表深圳在关键时刻说“邹老师,你来我们深圳吧”,为此,我们鼓掌。
几年前我听说邹老师参加气侯谈判的时候,当时我没有太多的机会向他请教,我很担心的一件事情是中国人长期以来的一种话语系统,就是你们都排放够了,现在该轮到我们了。如果是这样,一个崛起的大国就不是世界之福了。
今天这样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站在全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发展应该怎么看?站在全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碳排放在整个世界的扮演的角色是怎么样的而且在这个谈判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又有哪些博弈、互动。大家都非常关心。
而且深圳即将要扮演一个在人类历史上、从地中海到大西洋、到太平洋的过程中,能不能抓住一个机遇,扮演一个非常有创新贡献的角色的城市,可能就在脚下。所以这个时候邹教授来到了我们中间,跟我们探讨这个话题,非常的感慨。今天有很多的领导,有市领导、院领导都说把时间留给邹老师。
让我们掌声欢迎邹老师的讲座。
邹骥:津逵是我的师兄,上次在哈工大做讲座的时候,之后唐师长给我做评论,他的第一菊花就是说邹骥从蒸汽机说起,觉得挺惊讶的。说起蒸汽机就跟津逵师兄有联系了,我们是同学的时候,一起讨论这个问题是科技史,他是我们那一届乃至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清华社会科学系里面,在同学中谈科技史,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得人。
当时我们有一门课,由当年的大师来讲课,他们讲课的时候,我们听了之后心理是怀着更大的问题,就是所谓中国的现代化的问题,所谓中国为什么落后,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正好在五一节期间我又陪我夫人去西林看一看,到直隶总度看一下,回顾清朝的老师。号称是陪着夫人玩,其实是去做调研了。
为什么讲这个?
因为雄安特区的倡议公布以后,其实就是在那个区域,后来我说我们去看看现在的地貌是什么,若干年之后雄安初具规模又是什么样,白洋淀,西林,都去看一看。这个时候,包括我在参加气侯谈判的过程中,我曾经跟新华社的一个记者讲过,跟西方人交流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脑子里常常萦回的是从蒸汽机发明以来,那是康熙帝年间,1740年前后,咱们的康乾盛世,人家那边是发明了蒸汽机,迪卡尔,牛顿他们等等开创了微积分,后来法国的启蒙运动,那时候在折腾那些事儿。整个清代到明国,共和国,一步步的走来。
所以说思考气侯变化问题,我们要看科学、看技术,看产业,看人类现代文明的演进,看历史,看经济,看政治。后来也提出所谓发展中创新,因为当时提的时候,讨论气侯变化问题,二氧化碳、氮氧化物等等。后来津逵师兄跟我谈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就答应了。也是回报师兄对我的启发,讨论科技史,对我后来的工作、观点的形成都是基础的基础。
今天对我也是一个机会,感激师兄当年对我的教导,对我的关心和帮助。
确实应该站在文明的高度去反思这些问题,我想中国这个民族有很深的文化底蕴,今天我们站在国际社会里面跟人家谈,可以谈生意,谈项目,谈政策,这些都是要谈的。但是最终是怎么有民族自信心,怎么能够跟人家平起平坐,平等的站在一起,确实应该站在文明的高度。
说起文明,中国应该是有底蕴的,国人也应该是有自信心的。但是确实有时候自己迷失了,在文明的大路上找不到方向了,不知道文明是什么,不知道文明应该向何处去。当然今天我还没有这样的高度,那还要再高一些。现在国家有生态文明的学说和战略政策,包括这次总书记在“一带一路”的会上也在谈文明,从文明的角度谈“一带一路”,这个观点我也是赞成的。
但是今天我先从这几个方面跟大家方向,因为内容确实是非常多的,我也真的是没有时间专门准备一个专门的PPT,所以我就把以前跟领导汇报的,学术界交流的,先把相关的内容拼凑到一起,更多的是我自己看。因为我不做谈判工作也已经几年了,但是思考还是在的。我不会完全照着PPT讲,但是脉络是这样的,以防陷入到太细节。
刚才我谈到的文明、科技史,现代化,还是有些最基本的概念,帮助我们来达成共识,帮助我们一起探索这个问题,更多的概念、框架是起到组织作用。这个概念框架,还是起源于科学的认识,最早也是自然或者是物质世界里发生的事情。
我这里有一个脉络,工业革命发明了蒸汽机,大量的利用能源。过去讲科技史和产业史,工业化史,能源是一个脉络,能源也是一个标志。那个时候主要用的是煤炭,我们叫做化石能源,它的消费急剧增长,让人类的生产能力得到了指数级的提高,马克斯的著作里也说“人类的生产力成指数级的增长”,这个背后首先是能源指数级的增长。想起农耕时代就是烧点柴火,烧点木炭,现在有煤炭了,才能烧蒸汽,才能让纺织品的生产和消费急剧的上升,以至于英国本岛都容纳不下这些产品了,才能有了所谓的当时的殖民、扩张,是从这里来的。
大量的使用化石燃料,先是煤炭,后来是石油,天然气,后来又有核能,又转化成电。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让大气生态系统的平衡打破了,就是温室气体的平衡被打破了。温室气体在大概1750年前后,那个时候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大概是227PPM。到了今天,过了260、270年之后,今天大气中的温室气体的浓度过了400PPM,浓度急剧上升就产生了温室效应。也就是宇宙的辐射进来了,就出不去了,达不到平衡。出不去以后,地球表面温度就上升,这个上升大概在1900年到本世纪初,大概一百年间,地球表面平均温度上升了0.7度,当然这个原因科学界有很多争论,有的人说就是循环的,就是该上升了。古气象学家他们拿出几万年、十几万年,甚至是上亿年的古气侯的证据,表明气侯的温度是有周期的。
但是要单看这个,今天温度上升一点,不足为怪。但是温室气体的浓度可没有这么上升过,因为有怀疑论者不相信有气侯变化的事儿。但是有一个基本的事实,是这一次的温度上升,是伴随着温室气体浓度的上升,所以就极大的可疑,这次上升不是地球自己自身的温度周期,而是有伴随着温室气体浓度上升了,由温室效应造成的上升的概率就极大的上升。一个个体的人的生命周期,我们活一百岁,但是我们现在遇到的认知问题,他的周期是要超过100年的,有几百年。
比如说昨天晚上唐市长还跟我讨论二氧化碳的生命周期的问题,还有污染和生命周期的问题。实际上二氧化碳在大气中的留存周期能够到200、300年左右,甚至是更长。也就是说在乾隆帝时候排放的二氧化碳今天还存在,他也贡献了温室气体。这会产生一系列的负面影响,有一些显著的,比如说北极现在能走船了。还有很多著名的雪山的雪线,肯尼亚和坦桑尼亚边界的地方,他的雪线都是可以看到的,在上升,也就是在熔化。我们的珠峰,还有中国的好几个5千米以上的冰川,确实有证据表明他们在缩小,这不是某一个地方,如果在一个点上出现这个问题也不足为怪,但是在世界普遍的出现了这种情况,这就是在熔化。
带来的负面影响:首先也是有观测案例表明的,水资源的分布开始紊乱,老百姓讲的就是该下雨的时候不下,该下雨下雪的地方也不下,换着。就出现了很多极端的气侯情况,这个也是有统计的,极端气侯的频率是明显上升了。出现这种情况以后,水资源的分布就乱了,水资源分布经过多少万年、几千年,它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分布之后,河流、流域,人类的繁衍也顺着他,形成了一个格局。我们说黄河流域等等,这些都是几万年形成的。现在突然之间分布变了,但是人居的大的分布,包括生产力的布局、生活的布局,一下子是变不了的。比如说黄河的流量发生变化了,沿途的灌溉,沿途的工业用水,生活用水,那个一下子是变化不了的,就出现了很多的紊乱。
水资源的分布紊乱之后,就开始出现了对农业生产的直接影响。所以现在有很多科学家在全球范围内预测未来的农业生产率,气侯变化造成的极端气侯事件和气侯紊乱导致生产率的预期都在下降。深圳的金融很发达,如果你要买期货的话,如果要依据这些,我知道有一些保险机构是很敏感的,包括有跟我们做合作研究的,瑞士再保险,他们就很关注未来20年、未来30年,乃至更长时间农业的风险。但是整个科学的预期是说过去是靠化肥、农药、农业技术,甚至是靠基因技术来提高产量。但是也到了一个极限,比如说化肥已经不能再施了,施到这份上已经是水污染的问题,大气污染也挥发了。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对农产品的影响,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农产品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都是由于水资源闯的祸。
还有对海岸带的影响。前几天津逵师兄还转了一个关于珠三角的影响,我也看到过我们国家做海洋研究的报告,我们有黄渤海地区,有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的海平面上升是高于那两个区的,而且欧洲的很多岛国都出现了这种观测。大概是一百年里面上升了几个厘米,海水涨潮可以到岸上多走几公里。科学家断言,如果是任凭气侯变化的趋势这么下去,可能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能上升几十个厘米,那就有可能沿海的几十公里,至少是以十为单位的公里数会被涨潮所淹没。
首先会出现大量的盐碱地,有一次我去南通考察,南通就是冲刷长三角形成的城市,他们就出现了这种问题,地下水的水质开始发生变化。沿海农田的质量,更不要说沿海有这么多的经济设施,比如说中国的深圳、广州、厦门、上海,这些中国最重要的城市,财富分布最密集的城市都面临着这个问题。古代范仲淹的时代就修过威海大堤,延绵上百华里的地,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公路的路基。如果沿海为了防海水的涨潮,海平面的上升都要修这个,这是一个什么工程?这可是比修长城的工程要大得多啊。
另外是对基础设施的影响,公路,电网等等等等。
对公共健康的影响,这个研究现在还很初步。但是流行病学的研究表明,如果温度上升0.5度,对于青年人可能就是觉得热一热,多吃个冰棍,多喝点可乐就过去了。但是对脆弱人群,比如说75岁、80岁的老人,对于婴儿,可能他们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有一年法国热闹,那个温度才30多度,对中国来说简直就是凉快天,那一年并发症比常年就多死亡了4千多人。欧洲那个地方的夏天没有那么热过,大家在西欧生活旅行的经验就知道,很少有空调,夏天是很凉快的。现在温度是提高了哪怕是0.5度,在酷热天气涨了1度、2度,还会伴随很多的疾病就会出来。所以影响是非常广泛的。
面对这种影响怎么评估?
学术界的争议很大,有一位非常知名的经济学家叫做米卡斯顿尔爵士发表了一个“斯特恩报告”,他这个报告曾经做了一个结论:这个世纪气侯变化会造成的影响,要高于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的损失。两次世界大战中国死了两千万,俄罗斯死了三千万,遍地焦土。他进而说这样的气侯变化是人类历史上空间尺度最大,时间尺度最大的外部性。
有很多科学家在一个政府间气侯变化委员会上,2007年的报告,获得的是2008年诺贝尔和平奖,一半给美国总统格尔,一半给ITCC,我是他其中的一员,2千多个科学家,中国有40多人。理论上我也有一个奖状。有一次他寄给我了,是一个证书,诺贝尔和平奖。但是我不太好意思对外讲,因为还有很多敏感人物。所以我把这个证书一直放在我儿子的钢琴上。
这样的集体的发现,这是中国政府支持的,叫做ITCC,我们国家的联系单位是国家气象局。他们做的评估表明了这个风险是巨大的,所以专门有一个第二工作组,就是研究影响脆弱性及事业,就是对气侯变化存在着大量的脆亮的人群和受体。毫无疑问中国是比较脆弱的国家之一,我们的国土面积大,人口多。西北侧是一个非常脆弱的生态系统,那个地方水资源的一点变动,那个地方气温的一点变动,是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我说的短可能是几百年,在这个时间尺度让那个生态系统迅速的退化。我们已经承受中这种不可承受之重,这是我们国家的疆土。这样的脆弱性还体现在非洲、小岛国,这些基础设施不健全,防御能力比较低的国家和地区。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提出要应对气侯变化,他是一个全球的问题,这个事情跟你的信仰、宗教、国别没有关系。不管你信仰什么,这就是一个诺亚之舟,它出了事之后,不管你是什么国家的人,是什么政治信仰的,对不起,就是这条船。为什么霍金说人类还是要赶快离开地球?这是危机之一。而且在全球范围之内,科学界评估重大的风险问题的时候,气侯变化连续多少年一直是居于首位。因为这个东西有时候是在个体的人类里面不可逆的,你说升了再降下来?这个周期少则百年,多则几百年,是这样的。
顺便说一下,讲气侯变化经常说是要整一整了,雾霾多么严重?其实这是两码事,从化学成份上,温室气体在联合国的气侯公约控制上,什么二氧化碳,氮氧化物等等等等,一共有6种。精细颗粒物有很多东西,只要你的颗粒直径小于2.5微米都叫做PM2.5,小于10微米就是PM10,成分有交集的地方,但是大部分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我们要怎么应对这个问题?
有两个基本的途径,一个是减缓,一个是适应。
适应是什么意思?
我今天采取的行动不是立竿见影的,今天真金白银投下去了,气侯见效可能是百年以后。巴黎协定的目标是到本世纪末,离现在还有83年,那个时候的温升比工业革命的时候,也就是往前270多年,乾隆爷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温度比不能超过2度,是这个目标。如果是个体说,这个事情往前我也够不着,后也够不着,我跟着忙活什么?但是性质就是这样的,时空尺度非常大。
怎么办?
影响已经出来了,我现在马上要停也停不住,地球系统太巨大,太复杂,迟延太长。我就只能适应,既然热就得有热的办法,农业怎么适应,水资源怎么适应,人体健康怎么适应。
还有减缓,就是真的要减,为什么要提高人的效率,为什么要转变能源结构,这些事情都是现在必须得做的,晚做不如早做,早做又和你当前的发展战略,和当前的工业化的道路、城镇化的道路,和当前的技术,当前的金融,一切的一切都是有关系的,小则产业体系,说得更大是要改变你的文明。所以这个是减缓。
然后涉及到技术、资金、能力建设等等等等,几乎涉及到所有的方面。这就是我们考虑气侯变化问题的一个基本概念框架。
说到全球治理,现在主流的政策谈得最多的是全球经济治理和安全治理,这些谈得比较多。安全治理有联合国安理会的那套体制,我这里就不展开讲。经济治理,想到的是人民币的国际化,贸易有WTO,有双边的自由贸易谈判,这些都是治理的问题。怎么冒出一个气侯治理呢?我这里就把大家讨论得最多的三大治理问题,画了一个图。
有安全的有非传统安全,恐怖主义,互联网等等。气侯变化的负面影响也是非传统安全,他造成的结果不亚于战争甚至是世界大战。所以美国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气侯变化的决策部门之一,是五角大楼,五角大楼是美国气侯变化的一个重要决策部门。因为在美国当时协调的时候还有一个总统是国家的安全顾问,总统的几架马车,国务卿要参与,甚至环境质量委员会都是一个配角,总统是国家安全顾问。现在美国,比如说特朗普时期主导气侯的是总顾问,所以当时我遇到美国代表团的时候,我还说你们军方跟这个有真正关系?他说我们是安全的角度,有时候一颗原子弹也赶不上气侯变化。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
全球都有发展的问题,2015年还出现了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也就是SDG,在那之前有千年目标,而且发展议程一直是国际多变的议程,环境也有,全球的环境问题,除了气侯变化之外,生物多样性的问题,臭氧层保护的问题,国际水域的问题,污染物的问题,汞的问题,这些都是跨国的全球范围的事情。
这几大全球治理问题有一个交集,有气侯变化负面影响水质损害的问题,有抵御风险能力的问题,如果经济越发展,能力越强,基础设施越好,闹一场灾死不了几个人。最后是综合的战略和治理。
我试图用这张图来看气侯变化的问题在哪里,定位在哪里?
图中蓝颜色的部分,我试图在这里用最精炼的语言来概括全球治理包括哪些要素,有责任的问题,有权利的问题。有两个权利,一个是power,一个是影响力。你有什么影响力,说这个是我的东西,或者说这个东西不是我的。而Power是你的影响力,是你的话语权。哈弗教授讲软实力的概念,讲中国是不是崛起了,美国是不是衰落了,这个里面就大讲特讲Power,今天讲中国的power有一个体现在哪里,有一个非盟总部的大厦,有很多很好的体育馆,总统府,这些都是中国援建的。后来有人说这个就是你们中国建的,包括立交桥和北京的三元桥都特别像,但是里面坐的人都在对面的楼里培训过,说那是欧盟在那里办的培训班的基地,说你们负责盖楼,欧盟负责洗这些人的脑子。这些人坐在你们盖的楼里面干着对你们不利的事情,遵循欧盟的旨意。这就是说你有power,你有钢筋混凝土,但是人家能指挥他的脑子。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开始重视所谓的软实力了。
除了这三个要素之外,还有一个是博弈。一个全球治理一定是充满了博弈的,但是我们认定这个博弈一定是非零和博弈,不应该陷入真正的困境,不应该真正的是有你没我,非黑即白,他是有新型的博弈关系的。这里面有同盟,有竞争,也有合作。
外林的治理的有形状态要体现在机制上,为什么要有巴黎协定?为什么要有联合国气侯变化公约,这些都要有决策的过程,信息的过程。至少目前我本人对治理问题研究,我这个概念的边界大体是在这张图里。
当然我鼓励各位同仁进行扩展,我更鼓励你们去深化,把这些事情琢磨透。
如果把治理问题琢磨透了以后,我们在里面就更自如。
全球治理的基本要素,离不开一个进程,就是从不发达到发达的进程,蓝色的箭头是发展历程,发展阶段,发展水平。世界上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他们初步分成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但是这是政治的概念,特别是在联合国的政治场合下的概念。有时候人们要让你拿出一个标准却比较麻烦,你说人均GDP,有关系,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人均GDP比较低,但是里面有高的,沙特高,卡塔尔高,卡塔尔的人均GDP都到十万美元了,沙特也是三四万美元,比欧盟国家还要高。你说他是发达国家吗?不是,他还是发展中国家。他是没有发展的增长,他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经济结构单一,如果油价一落,他的财政收入就完了,他的经济体就要出问题。俄罗斯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样的经济结构,包括委内瑞拉,这些国家出现动荡,都是因为他除了卖油没有别的太多的收入,70%的财政收入,GDP都来自于石油。但是他依然是发展中国家。
我无意在这里做出什么定义,但是有一个相似的概念,叫做中等收入,高收入。这两个概念有关系,但是性质上不一样。一般说中国现在是中上等收入的国家,这个一般来讲是用世行的标准,世行为什么要定这个标准?是确定你有没有资格获得贷款。中国反过来还要出资,去给别人贴。中国现在大概是8千美元,一般到了1.2万美元,按照世行贷款的享受权利的标准的话,1.2万美元是高收入的国家,那就绝对永久性的。这个和发达、不发达是有联系的。发达国家一般肯定是高收入国家,但是这两个的中间有一个除和贷,刚才讲的石油输出国是一个例子。另外更重要的是回到昨天唐市长跟卧谈的,讲发展的形式,经济结构在这里面是发达还是不发达的重要标志,除了人均收入水平之外,还有很多是人类发展指数,社会治理,文明程度等等等等,政治的开明程度等等,这些我不展开讲。但是我们基本上的思路还是沿着一个发展的进程去看,因为这是联合国下面的谈判和治理,我们只能用联合国的概念。到今天依然是一个政治概念,比如说新加坡就算是这个集团的,谁也不认为他是一个穷国。
所以我们依然还是用了这个概念,所以现在基本的格局也是发达、发展中,在发达国家内部和发展中国家内部又有差异,这是我们认识利益相关者格局的一个基本结论。
相比较哥本哈根的那次,2009年的谈判,在1997年的时候京都议定书的谈判,以及联合国气侯框架公约的缔结,到今年已经是25年了,发生了什么变化?最重要的变化是把最不发达国家摘出来了,有一个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发生了分化。新兴发展中国家最核心的是中国,我们依然承认以往政府划分的阵容,中国在政治上的身份认同上依然认同自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也确实是发展中国家。
我有一次跟一个岛国的大使在联合国和中国有一场争论,他就直接说中国已经不是发展中国家了。我说还是,因为你们同胞说了,路易斯有一个二元结构理论。我说中国今天这个二元结构还在,就这一条,中国就还是发展中国家,而且农村人口和欧洲农村人口的概念不一样,欧洲农村人口是富裕的象征,中国农村人口是低收入。津逵有更多的研究,我说我们的比重太高了。另外中国的中产阶级,现在还不是社会的主流,尽管跟其他阶层相比,已经在社会上影响力是更高的,但是官方统计这个比重大概是20%左右的人口占比。按照高盛的来是,按照纳税的算,这个比重可能只有10%几。这样确实就此而言,说你是发达国家,还不说社会治理这些,确实是离得太远。他当时还挺不好意思。
我想你都当大使了,还不知道这个事儿,学是怎么上的?还是在美国上的学呢。
但是中国在认同上这一点,我现在同意中央对中国的定位,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且这个事还得要几十年的时间。按照真正世界的国际标准来划分,我们还不是说人均GDP到了就是发达国家,你的经济结构,技术的竞争力,社会治理能力等等,包括人类发展的指数。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朴素的指标,就看社会保障,就看老百姓的社会保障。如果社会保障不管是覆盖率,我们是全民覆盖,那个没用,农村的社保得不起一场感冒。真的比较70%、80%的人口享受到比较充分的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养老,就业,这个时候大体标准就算是发达了。
这也让我想起了为什么伦敦奥运会的开幕式的团体操比赛一定有一幕是讲护士,讲医疗,这是他们国家的骄傲。这是一个国家发达程度的象征,而且真正是体现在人民身上,并不是真正体现在某个巨大的工程上。
为什么我多说这些?
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很大,中国到底是谁?你姓什么?从哪儿来?要往哪儿去?现在是一个什么状态?整个国民要不断的反省,不断的定位。当时津逵讲人类命运共同体、责任,这个事情和定位是密切相关的。
在这里讲他们的影响力,讲责任,讲权利等等,发达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他的优势和利益,因为发达国家有一个观点,我们有争论的,他说他用一般的《民法》的原则,就是不知者不为罪。说92年才有联合国的气侯变化发展公约,之前的事情不能追究我,那个时候我们哪儿知道?而且你们一追究就追求到了工业革命的时候,那都是康熙帝的年代了。但是我们有一个不同的观点,无论是作为企业还是个人、还是国家,你爷爷,你爷爷的爷爷,那时候真的不知道气侯变化的事情,排放就排放了。
但是这是作为国家之间的判断,作为国家不应该是这种态度,我当年确实是不知道,但是我承担责任。因为你今天国家的有利地位跟世界题中的优劣地位,今天国家的基础设施是跟那个有关系的。要不然咱们换一换,我也吃香的喝辣的,我今天在这个产业链里面,我是在打工,是由于你们历史上已经建立了这样的一个地位,那么我就只能是打工,你是老板,你拿大钱。咱们就不抱怨这个事情,但是你说整个气侯变化的事情就没责任了吗?这样说也不好。
就此而言,我们经历了一个思想的变化,和92年的时候,中国人均GDP,可能那个时候不过1千美元,可能只有几百美元。我记得1982年中国大概是200美元,到了1992年,每年涨10%。那个时候你的地位,你的眼界,你的能力,也只是那样的观点。
但是到了今天,已经人均8千美金了,已经有了4个一线城市了,也已经有了沿海地区的先进的经济资产,再来看看你的能力,你的需求,比如说老百姓对环境指标的需求,那个时候是叫光脚不怕穿鞋的,我没什么好牺牲的。但是今天可淹不起,大连,青岛,宁波,上海,厦门,广州,深圳,这些都是我们的掌上明珠,这些是不能淹的,多少人口、财富在这里。今天我是有包袱的人了,也是小中产了,所以我的立场,对于气侯变化这个事情,从我的利益上来讲肯定跟当代不一样了。
再一个中国在海外的投资已经累计上万亿了,中国已经在国际上要赢得尊重了。另外,全世界的事儿中国干得好不好是有影响的,影响也很大。你不能说这个事情跟我没关系,得正视。而且中国这个国家,我们之所以5千年能够延绵下来,还是一个讲德讲义的国家。这和很多国家不一样,如果我们丢掉了这些,丢掉了自己的德、义,责任感,丢掉了天下大同的理想,有福同享,有祸同担。另外我们有天人合一的哲学,这些东西丢了就没有身份了。
有了这些之后我们是有文化的民族、国家、人,这个世界就会尊重你。没有这个,就如亚洲某国家一样,拼命的要搞核武器啊,就变成了那样的国家。很显然世界需要怎样的国家,这个是不用多说的。
所以中国就摆在了中间,大的定位是我还是发展中国家,但是我是一个新兴的发展中国家,我有自己特殊的能力、地位、责任。而且这里面更重要的责任是在于中国是有条件走出一条新路子的。这样就确实是要靠大国来做,大国是有各种格局,增长方式,发展中的创新。
人类历史上经过3次,或者是正在经历第3次的发展浪潮。第一次是从工业革命一直到战后,主要是在欧洲、北美,加上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他们大概汇集了10亿人口,现代化成功了。他们的环境,对地球的生态系统有一次扰动,这次扰动很大。但是幸运的是那个时候地球的生态系统容量也很大,所以就包容了这次扰动。但是最后也还是出毛病了,所以就出现了60年代的环保主义的思潮,以及人类环境发展大会,从那之后人类对工业革命的反思。这是第一次扰动。
第二次扰动发生在中国,又是10亿人的数量级,搞了一次现代化运动,或者是工业化、城镇化的运动,而且成果很显著。这一次还是很扰动,没有幸免,对环境的冲击还是很大的。实事求是的说这次冲击采取了一些措施,应该比发达国家的那次冲击是要小一些的。但是自然系统的承受力又弱了,因为以前已经有累计量了,很多的温室气体主要是靠累积的,所以我们还正在经历中。
现在第三波浪潮要来了,非洲、东南亚、印度要搞工业化了,他们这一波起来是几十亿人,他们的前面有多很路可以走,技术的,体制的,观念的选择,所以为什么中国现在要提生态文明,提绿色低碳发展,这个一个是中国自己的事情,实际上马上也是给人家的下一波,你的一带一路,要上多少万亿的投资。这几天习主席讲我们的国开行,进出口银行的贷款,一下就是几千亿,要往基础设施里面投,有一个杠杆,就会带动几万亿。这些投资是怎么投的?什么技术选择,什么空间配置?什么样的理念,什么样的管理。这个冲击就是第三轮的大发展带来的影响了。
所以说中国的作用,我没有系统的归纳,但是我想我们要意识到现在除了对我们自己,对雾霾重还是轻,水是不是干净,除此之外,在全球的影响,看得见,摸得着的,也就是我刚才说的,马上你的铁路怎么修,公路怎么修,电厂怎么修,能源结构是怎么配置的,将来你设想的这些基础设施,他支撑的消费模式是什么?这些都出来了。
所以国际上现在对中国的一带一路的战略还有一些疑虑,其中之一就是会对地球的生态系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所以中国的作用,中国自己的身份认证,不能说反正你先污染了我也来污染,你就不能说我。今天已经不是这种话语环境了,因为如果你还那么做的话,对全球的影响是不可逆转的。
而且我们也看到有机会,就是俗话说的一天还洗两次澡,但是能不能不那样了?过去说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是不可能的。今天由于科技的革命,我们看到了曙光,看到了可行性。
全球气侯谈判是谈什么?要谈几个问题,一个是长期目标,还有中期目标。唐市长带着我们在哈工大研究规划的时候,我提了几次建议,要把时间尺度扩到2050年,也是呼应国际的进程。这个也并不是说太高大上了,为什么不远?我们基础设施投资的周期大体就是这么长,一个电厂投下去,标准的周期是35年,实际用40到45年。今天数到2050年才30多年,还有33年。
包括最近大家看中美贸易谈判,我两年前给中央曾经提过这个建议,当时我没想到是特朗普,我当时想到的是气侯变化的谈判变成了中美的亮点。你还能怎么再亮下去?字也签了,手也握了,两国元首的文章是做透了,中美之间没有为一件事,两国元首在两年之间签三次的,没有。
天然气为什么要讲?就是本世纪中的战略。为什么要讲巴黎协定,国家一定要定这个战略?就是后面有一个直接的,你的好多基础设施的设计是要在这个时间尺度里来安排的。当时中国前些年是盖一个楼,不过五年时间就拆了,这种事情还特别多。先把30年的大计搞好,一开始就要考虑长远一点。当时我对天然气的想法是我们现在的能源结构,三分之二是煤,这个是难以为继的。我们设定了个愿景,到2050。有了愿景之后再论证到底怎么走,再安排,如果连想法都没有就麻烦了。有了想法之后,不断的做中间路径的探索,就会安排得越来越实,可行性随着科技的进步,就越来越看到了可行性。而且历史也老是教育我们,我记得80年代初,读托夫勒的书的时候特别激动,觉得这个简直就跟《海底两万里》的科幻小说一样的,今天回过头来,他的想象力远远低于实际的进展,至少还没有谈互联网,更没有谈移动互联网。
我们今天想象的能源,讲30多年以后的事儿,也许我们想象不到,历史证明人类的想象力总是落后于实际进程的发展,这是历史的证明。
如果2050年三分之二是可再生能源,中间怎么过渡?要我明天就三分之二真的做不到,技术、体制、观念上都做不到。但是一个国家要30年之后,能源结构要发生变化,应该有这种战略。就好比60年代英国人就开始有香港要被回收的感觉,差了30多年。他之前就开始了,智库就开始论证这个问题。我们今天提前30年安排一下中国能源的基础设施的布局,应该要有这种眼量,因为今天巨额的投资,这个投资是几千亿、几万亿的投。
我就想到了一个过渡的办法,也不是多么复杂的证据,根据历史的证据,这一个过渡30年用天然气来过渡,迅速的用天然气来替代煤,而且有步骤。第一步,煤炭的结构是50%的煤是去发电的,30%的煤是工业冶炼的。还有20%的散煤,大家吃烤串的时候,还有郊区周边农民,特别是京津冀地区农民他们烧的占了20%,中国的五分之一是了不得的,就是六七亿吨的煤炭,可能整个欧洲也没有这么多。
我迅速的用天然气把这个煤替代掉,我们的雾霾问题会大大的改观,而且可以设定5年目标,10年目标。再说工业污染,再说电,一步步的来。这样迅速的有减碳的效果,而且国内有减雾霾的效果。天然气的能效高,又节约了很多的煤。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这些都是一步一个脚印,都是有针对性的,散煤,工业过程的煤。电煤的50%不动他,很多电力部门的人来找我争论,说我们这才投了10年就要我们拆?我说没有这个意思,放心的用,但是你能发多少电是我管不了的,你的机子我留着。但是我给你足够的时间去消化你的固定资产投资,让你赚足了钱把贷款还了。但是你们现在要做好准备,到了2040年,2050年,你们这些电厂的废铜烂铁,拆,这个时候你不心疼、不可惜,因为赚足了钱。那个时候要准备好大量的能源、电力是可以替代的。但是这个中间用天然气,基本上是欧洲和北美的历史依据,他们的能源经历了由煤到天然气,现在德国做得最好,可再生能源已经到30%,但是也到了某种瓶颈。但是这是一个有历史证明的,对应的空气质量也改善过来了。
有一些科学家跟我争论,说天然气更导致雾霾,我说你给我讲个故事,能够自圆其说。但是我要一个历史证据,如果是这么说,欧洲发现了天然气,英国煤改气了,雾霾应该重了,事实证明他们的雾霾下来了。对应的历史事实是他的煤炭会大量的被天然气以及其他的能源替代,这个事情而且在技术经济可行性上也是可行的。
现在国际能源贸易结构正在发生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北美的异军突起。精英们特别不看好特朗普,但是他做了一件事情是顺应了能源结构变化的潮流,他有两件事情,一件不靠谱,一个是靠谱。不靠谱的是弄了20几个煤矿的矿工,怎么可能把美国的煤炭再搞回来呢?市场上的发电价格,天然气早就远远低于他了,哪个投资商,哪个出资人还敢用一个没电厂?你让矿工回到煤电厂,谁用?这个是不靠谱的事情。
但是有一个靠谱的事情,大力发展天然气,前几年热议的能源独立,这个是靠谱的。但是这样带来国际的能源生产和贸易版图的变化,过去以中东,以oppace为出口的油气出口,现在遇到了北美的强劲的挑战,而且北美有望在未来的5到10年中,变成世界第一大油气的出口商。这个现实我们是要看到的。
现在正是了我当时的判断。加上特朗普的政策,就上升得非常快。这个油气美国本土是肯定用不完的,美国现在存在着巨大的贸易赤字,他的油气在日本福岛以后,有大量的核电厂关了,上天然气。主要是进口美国的天然气,一年300亿美元。中美贸易赤字去年是3600亿美元。假设中国进口和日本一样多的天然气,那么我们的中美贸易赤字能为此减少大概10%左右,光是天然气一项。突然发现一个新的概念出现了,或者是一个新的利益共同体出现了,从中国而言, 现在的雾霾已经很头疼了,要花多少钱治理雾霾。能效瓶颈也出现了,需要提高能效,这个时候有天然气替代煤,是一个可行的选择,尽管谁也不敢说这是最优的选择,但是是可行的。算价格,算投资,算成本,算技术的可靠性,都是可以做到的。而且可以马上的,非常迅速的让雾霾见效。为什么环保部以前任的一个副部长,老百姓问他我们的雾霾还得治多少时间?他说的是30还是40年,一下被老百姓骂下去了,说这个不是等于白说了吗?老百性的心情,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那么有没有更快更靠谱的办法?就是天然气!而且现在投下去,一个投资周期20、30年,到了2050年的时候也敢拆,敢淘汰,因为钱赚足了,那个时候的可再生能源上去了,而且现在做正好可以填补这二三十年的空白。
这是对中国的好处,就是经济越发达,需要的能源也在升级。天然气绝对是比煤好。
唐市长跟我讲,他做市长的时候,深圳当时一个重要的决策,现在回过头来发现很英明。深圳之所以比较早的过了雾霾的拐点,跟当年大胆引进天然气是非常有关系的。据说当时进的天然气都没有人要,后来是深圳和广东省一个城市拿了一半,当时看了是很贵,现在回头看功德无量。越往后越不差钱,你的收入还在提高。所以今天至少跟全国比,我们的空气质量好一些。唐市长大概是十年二十年前的决策,弹指一挥间,如果今天下决心,比如说京津冀,国家的能源结构大规模的上天然气,大家还是会说贵,是贵。但是说清楚一件事情,花得起吗?花得起,拿钱换气,就好了,雾霾少了,能效上去了,什么都现代化的国家,什么都物流的国家。让美国那边有益,他出口天然气,弥补他的贸易逆差。这是特朗普为什么要搞贸易保护,确实是赤字受不了。创造了多少的就业机会,我在你那里提高油气的产量,又搞输油管道的建设投资,搞港口加压设备的投资,加大运输,一系列的就业机会和投资机会就出来了。这些美国经济没有问题,因为有好处。
为什么我还是博弈,一定是非联合的博弈,我们要找机会。你有好处,我有好处,有的时候是自然出来的,有的时候是需要创造机会,有的时候是需要识别的。你识别的这个机会,这个博弈变了。我们当时工作的时候,习主席和奥巴马在谈判的时候是谈的美国减多少,中国减多少。而今天跟特朗普不是这样的博弈了,他说我不减,看着这个小子很混,也不对。但是毕竟是美国总统,美国大选赋予了他权利,我们要面对现实。对于保护气侯的人,我们发现如果他能够顺畅的,以合理的市场价格卖给我们大量的、足够规模的天然气,这个减排的战场在中国。对于全世界,全球来讲是一件好事儿,而且中国减的排,说老实话,现在老是说特朗普把奥巴马的气侯变化计划取消了,美国就完不成任务了,我说照样完成。这个我们知道,奥巴马说起来形象很光辉,保护气侯,其实谈判的时候奸着呢。他给自己谈判的余地留得多多的,基本上不用费太大的劲,就可以达到这个目标。
首先是他的煤电的电厂是EPA,走了一趟程序。但是没有这个,我相信市场的力量足以让他的这些煤电厂自然就淘汰了。市场价格就摆着的,一度电,用煤发电是多少美分,天然气是多少美分,这是摆着的,谁还会投这个贵的?又脏,又有风险,又有重金属,那是不可能再投煤电厂的。
所以我觉得美国的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了,技术经济的性价比已经变了,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当然不能否认美国政策的作用,但是他的经济发展阶段,技术经济的状态又到了这个阶段,就该问下走了。
所以就此而言,我们发现一个新的概念。我跟你就不谈气侯变化了,谈能源合作,谈贸易的合作。所以这次十大贸易的进展,有一个天然气,为什么专门钢天然气?而没讲石油?没讲别的?我就告诉他了道理。
所以我预期在未来,天然气可以注意一下,特别是中美合作的天然气,商业模式已经形成了,有人说这个影响了中国的国家安全,美国鬼子把气源一断,是不是对国家的安全不负责任。我说没有那个事儿,这个很好办,从美国的气田开始就合资,美方51%的股,我49%的股。你的输油管道,港口,加压设备一起投,运输公司就是国际上的船,能运就运。到了中国,还合资。让美资进来,中资51%,美资49%,这种商业模式谁卡谁的嗓子眼?卡不了,有钱一起挣,而且这种事情越多,中美关系就越稳定。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发展是两国人民的福祉,我公开的跟很多学生说过,我有一个小孩在美国读书,92年出生的,难道我们的工作就是想着打仗,把我的孩子送到战场吗?谁愿意把孩子送上战场?我们要做的工作是要避免这种情况出现,我可以让我儿子娶个美国媳妇,这事儿是可以同意的。但是我不愿意让他跟美国人打仗,反过来美国人也应该这么思考。
我们一起繁荣嘛,一起发展嘛,你也不说谁是TOP1,TOP2。
在考虑目标的时候,要有这个时间轴。还有一些基本原则的问题,管理模式,承诺力度的问题,就不展开讲,还有要做协定的要素的问题。
今天不是专门研究巴黎协定,我就非常快速的过去。
气侯变化问题的定性有环境问题,发展问题,也有建立全球气侯治理的问题,治理的问题核心还是责任,承诺,以及相关的机制。
问题的实质与出路,胡锦涛时期有一个论断,叫做:气侯变化问题源于发展,解决也要通过发展来解决。是一个发展的问题。
基本的论断我是赞成的。
考察了排放源的历史,排放强度的历史,我们认为也确实是。为什么我们要从工业革命谈起,从蒸汽机谈起,是归于这样的认识。排放历史的描述,特别是二氧化碳,他的生命周期特别长,有大气中累积的问题,还有不同的部门,不同地方,国家排放的问题,来源结构是很复杂的事情。我特别想强调的是瞬时排放和累积排放,大气中的温室气体的浓度,静态的浓度是温室效应的基本的决定因素。大量的排放之后循环不回去了,这是基本的科学原理。
这个累积和瞬时排放又有联系,就是某一个时的加起来就是累积牌坊,今天大气中400PPM的浓度,首先累积是来源于发达国家当年的排放,发达国家占比能够占到70%左右,但是这个比例确实在下降。发展中国家的比重在上升,其中中国的比重上升得尤其的快,这是毫无疑义的。
瞬时排放中国现在是第一,而且这个第一的地位是远远超出了美国的第二。但是在话语的过程中,谈判的话语权上,话语的语境上,美国、欧洲愿意谈瞬时排放,一说中国排放这么多,你是第一大排放体,你不减排谁减排?这个话也对,也不对。对在于第一大排放体,累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累积排放就要超过我了。不对的在于你不能拿这个做指标来分配责任。我们应该用累积排放的量来作为责任的基础,也就是说我是该减,但是你不能逃避你的责任。这两个指标代表了两种观点。
排放水平上,什么来决定排放水平?这和发展路径是有关系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排放 的强度是不一样的,农耕时期那时候没什么排放,今天到非洲去是南天白云,但是你能说这是你的理想吗?似乎也不是。你到欧洲去,到北美去还是蓝天白云,但是已经很发达的蓝天白云。中国印度在哪儿?离开了非洲那样的田园牧歌的蓝天白云,又还没有走到北美和欧洲的蓝天白云,正是乌烟瘴气的时候。大兴土木是干什么?后面就是要炼钢,就得有水泥,就得有重化工业,但是中国又比印度早走了一段,我们的钢炼得现在产能开始过剩了,水泥产能也开始过剩了。房子也还在盖,速度远远没有之前的速度和强度了。2003年到2010年时候的强度太高了。
中国正走在半道上,但是要看到不同的发展阶段对炭的要求、强度是不一样的。到后工业社会的时候,你的产业、服务业,产业链,你是在高端,你赚钱,你来收入,是靠你的知识产权,靠你的品牌,靠你的咨询。大量的制造业,按照当时传统模式可能不在是那样了,但是不意味着中国不赚钱了,这各是跟发展中有关系的。但是我们知道发展中是需要创新的,是有条件创新的,创新点在哪儿。
另外是全球治理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不是为了治理而治理,我的治理要解决能够把人类的发展路径,在新的时代找到新的路径,如果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治理是成功的治理,是一个有的放矢的治理。这是关于增长方式发展路径创新。我建议这个要作为中国气侯变化的国家学说,这是我在几个场合,最高的一次是克强总理在2015国务院气侯变化领导小组会议上的讲话引用的这句话。去年的杭州峰会用了“增长方式的创新”这个词,思想是大同小异的。既然已经在官方高层次都呼之欲出了,智库就应该把这个凝练出来,应该给决策者,这就是国家学说,旗帜鲜明的说。中国关于气侯变化的一切都要归结到发展路径创新上,归结到增长创新上去,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这个思想是怎么来的?
今天说起来好象是一套一套的,其实是在实际的争论中产生的。我特别受刺激的是2012年,当时从WR转到国家气侯战略中心,给我的主要任务是支撑气侯谈判。我们当时看到的政府文件是一条一条的,坚持什么什么原则,每次一宣誓政策就是这么说。我们在国际上跟人这么说的时候,人家记不住,再加上生态文明,加上稳中求进,加上这些词,国际上对这些词也晕了,半天都听不懂。后来南非提出一个公平参考体系,巴西提出一个同心圆的理论,一提就马上抓住了人心。我说中国很费劲啊,老是讨论讨论就被边缘化了,你提的几点建议,别人的话语体系听不懂,也记不住,也不是这个思维习惯。后来我就想不行,这一百多个国家在这里辩论,炒得一锅粥一样的,怎么样让中国的观点。你说完了之后就没有人再提了,哪怕是反对的也不再提了,这个局面不行啊。我们老是希望里面写点我们的东西。后来一想可能写16字令,写对仗的东西还不行,这不是国际语言。后来我们就在想应该把道理讲清楚,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发展框架下讲发展的路径,其实是根上把事情说明白了。好多学说还不是我们自己发明了,刚才我谈到了路易斯的发展理论,谈到了ITCC的表述,我们把这些综合起来,总得有一个标签。
中国的观点是发展路径创新,我有时候以权谋私,让我政治代表的时候就老是引用一些研究的成果,其实是我自己的成果。后来发现底下就听进去了,有相当多的谈判代表,相当多的智库就来找我辩论,说你的意思是不是你们现在的发展阶段就应该多排,我说不是,还有“创新”, 什么是创新?就是以少的排放达到同样的发展水平,我跟你争的是发展权,希望我的人民也能过上跟你一样好的日子,享受同样的社保,同样的社会保障,一样的生活质量,健康,自由。但是我们要比你们当年的排放要小,是这个意思。
责任方面,发展路径你们也有责任创新,不能说过去排放高现在就要永远高,咱们要一起使劲,现在又是全球化的环境,咱们的技术得共享,贸易上一起想办法。他们觉得这个是能够说得通的,慢慢的就听进去了。
而且这个里面也蕴含着中国的战略本身,这个时候我们不是一味在谈90年代,重点强调区别,你减排,我还得继续排,因为我是后来者,这是当时的基调。但是我们强调发展路径创新的时候,咱们就一起创新。欧洲想想怎么创新,美国想想你怎么创新,我再想想中国怎么创新。当然创新的路径可能不一样,说法也不一样,但是目标是一样的,而且效果可能是大不一样的。总而言之说到这个根上以后,我从欧洲的工业化史说起,北美的工业化史说起,现在该轮到我了,我怎么吸取你的教训,怎么记住你的经验,这么谈是有历史依据的,有事实背景的。我们今天也在追求工业化、城镇化,我们的国情也可以说出来。
所以我想这样的道理,是能够让人至于世界民族之林,能够摆到一个共同的道理上,有共同的价值观和目标,又有我们的国情、困难、主张、作为。
这就是今天上午跟哈工大的老师讨论,这些都是实证,纵坐标人均排放,横坐标人均GDP,最上面的线是美国,唐市长昨天讲的,70年代就到了峰值,经历了一个大平台,这个平台里面还有波动,07年以后往下走,这是美国。但是美国再怎么样,你的人均排放还是世界老大,你凭什么那么高?这就不够低碳。
说到这里不闹情绪,但是美国人也不要优越,不要说你老是救世主,你现在不是。现在你训不着我了,总书记讲的第一句话“气侯变化问题,西方人没有资格指责我们”。但是中国也不要沾沾自喜,你的8吨还有8吨的问题,这个是德国,绿线是英国,他们大概的规律都是有一个峰值然后下来,这是中央在决策承诺巴黎目标的时候,为什么这一次和五年前的哥本哈根比多了一个峰值的目标,这就是最基本的东西。
我去气侯中心工作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图画出来,克强总理看到以后,说这个是我们找到了一个国际上比较普遍的规律,这是事实。其实很简单,但是这是一个争论不休的曲线,大家都有峰值,为什么中国就没有?所以中国也得有。但是中国的峰值在哪里?中国现在刚发展到这里,横坐标人均GDP,后面的是模型模拟的结果,是虚线。发达国家大概的人均2到2.5万美金左右达到峰值,中国做了很多推演,基本的结论,人均大概1.4到1.5万美金的时候就可以达到峰值。这个换算成时间,大概就是2030年前后,实际上应该是2025年前后。但是为什么说2030年?因为这里面有一些误差,总不能谈了一个中国违约,这也是不行的。所以要谈到我们心理有谱,可能2025年能到,但是谈判到2030年,如果25年到了就是提前完成任务,别到时候30年才完成任务,在全世界面前还拖了五年,就对国家形象不好。
别人是2.5万美金为什么你是1.4万美金?这就是后发优势,现在修的深圳、北京的地铁肯定比一百多年前伦敦的地铁要先进,今天炼钢的技术,做水泥的技术,肯定比他一百年前,50年前的要先进。中国今天的煤电厂比美国的先进得多。所以是不一样的。
另外今天已经有主动的政策和战略去做工作,那么中国有可能在1.4、1.5万美金的时候达到峰值。这么扎实的数据工作,科学研究系工作做完以后,把国家的道义制高点就勾勒出来了。美国到22吨,人均GDP2.5万美金达到22吨,中国1.4万美金达到8吨、9吨,谁做得好?从历史的指标上来讲,谁对人类的贡献大?谁创新了?这个时候坐在那里,你要跟美国人比有优越感,中国人现在做的事情,作为一个民族,作为一个国家,比美国人可是做得好,比欧洲人做得好。
把这个事情摆清楚,我现在要做一个前无古人的事情,别拦着我,我要创新。别拦着我,我现在要做一项伟大的事业,你们应该为我鼓掌,我应该在这个治理里面做一个好的表率,而且这个事情要给发展中国家看,穷兄弟们,不要跟美国人学,不要跟欧洲人学,咱们现在要做一个更积德的事情,对子孙更功德无量的事情,我们能够做好,我们的收入还要往上涨,但是我们的排放是往下走的。这个事情是靠谱的,要告诉纬度,告诉东南亚,告诉非洲。能用LED的就不要用白炽灯了,能用变频空调就不要用传统的了,就是这个曲线让中国在治理中的话语权发生了变化,我们的形象也变了。
这就是习主席说的第二句话“这个事情不是别人要我们做,是我们本来自己就要做,就应该做”。
回来就落实,这个线也不是回家睡大觉就可以自然而然的有的,还得努力,得有投资,有研发,有体制的保障,有政策的引导,才能走上这条线。所以回来就要抓落实,就是习主席说的第三句话“要抓落实”,为什么要环保督察,为什么要花大力气,为什么要总结深圳的经验,都是要保证这个虚线能够成为现实。
这样再回过头来,中国的发展路径是不是创新的?要把这样的道路掰开了,消化了,再跟国际同行说。整个问题的核心在认知上把这个道理想透,想明白。
增长率是等于两个增长率之合,一个是要素投入,劳动力的投入增长了,能源投入增长了,资本投入增长了。再加上一个要素效率的增长率,这是一个基本的模式。
过去改革开放前30年主要是靠要素投入,投资来支撑高增长,10%、12%。现在的这条路走到头了,产能也过剩了,劳动力的红利也没了,人口红利也没了,你还靠他来支撑你的10%是支撑不了的,就得主动的转变,要把它提上去,要素效率的增长率。
能不能以这个为主要的核心的线索,去看看怎么通过提高要素生产率,一方面支撑长期经济的增长率,另一方面可行。这个要素,效率就包括了能效,包括水效率,土地效率,矿产效率,环境质量效率都在这里。
现在的问题实质是要一个更可持续的、更靠谱的增长率。因为如果我们还据守在这个增长率里面是死路一条,就是中等收入陷井。如果能够转到这个增长率支撑的话,那么我们就是光明一片,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梦想的目标就有保障,这就要求我们去做改革,做经济增长方式的创新,调整结构。所以说发展路径的创新,核心含义在增长上。
包括全球和局地的环境资源约束趋紧资源环境要素投入效率加速提高。过去是靠污染,靠侵蚀自然资本的原始资本积累,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要找到新的生产要素,这就是知识,就是技术,就是治理和发展的理念,要调整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要更多的用人力资源,还有知识资源,而更少的用自然资本。
这就是我们学说的基本思想。
要素比价改革要跟上,让资源更贵一些,就是要比价。
全球治理和巴黎协定就不展开讲了,里面有利益相关者,把治理的利益相关者的方方面面都归纳到了一个圆圈里面,权利和责任是怎么划分的。
这是现代政治操作里面的一个启示,也就是一到联合国就是代表了中国的利益,马上问中国的利益是什么?一句话还说不清楚,因为有东部有西部,有高碳的部门也有低碳的部门,有煤电的部门,也有煤炭的部门,还有太阳能,还有风能。你代表的是谁的利益?后来我想是有一个结构分布的,今天的不管是中国,任何的一个国家,他都是多元利益组成的一个利益体,怎么凝聚成一个国家意志、国家利益?这里面有技术和创新能力,有公众的意见,城市的中产阶级,他们对于雾霾简直是太迫切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一就是蓝天。到了农村,往北京出去一百公里就在烧秸秆,他说蓝天不是我的大事,宁可赌死也不愿意饿死。再去五大电力集团,两大电网公司,跟他们聊一聊,说这个巴黎协定是真的假的?出去说说,回来咱们怎么做,我的煤矿怎么样,煤电怎么样,还跟你讨论这个问题。而且也有说能源安全,说三分之二的油都是进口的,怎么替代?怎么保证安全?
有一些沿海城市要说海平面上升,对于我们是个事儿,一些农业,一些水利设施,但是谁代表了农民的利益?说我脆弱,我受气侯变化的影响吗?我的产量可能受到威胁了,他们自己可能都不知道。另外是朝阳的低碳产业,说太阳能的政府还打了白条,补贴到不了,资金链断了。把这些意见都摆在这儿,他们都反映到各个部委,工信部的意见,环保部的意见,财政部的意见,发改委的意见,你听谁的?这个时候怎么凝结成国家的利益?因为这些利益经过政治体系的各个部门的作用太多,口径都不一样了。哪个部门主导?环境部?外交部?还是谁主导?最后出来国家利益的表述是不一样的。
我们国家立场和政策的选择,有气侯的脆弱性的利益,有能源安全的,高碳经济的,公众的意见,技术创新,能力等等。看国家利益的这张饼是层出不穷的,谁的利益更大?谁在这个布局中占更大的比重,谁更有影响力?这里还涉及到社会公平的问题,有相当大的人口是没有话语权的,但是他是相关的。这个时候我们对于国家利益,到国家立场形成的判断,和形成的过程,我没有结论,只是把这个事实摆出来,但是对于研究者来讲,我们就要思考,最后什么是对国家长远发展,对更多的人的根本利益,他是更具有代表性的。我们要用这种观点看问题。
具体的巴黎协定有关的我就不展开讲了,有责任,责任的内容,责任划分的依据。还有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巴黎协定的内容就更不能展开讲了。
谈判过程和影响因素,外交界的人听得津津有味,过程本身又分了几个阶段,有一些主要的里程碑,谈判具体的安排是什么,四年的谈判时间是怎么做的,谈判过程如何组织,这些都是参加全球治理的一些具体操作的手段。我们得懂操作,老是说要懂国际规则,国际规则在哪儿?这些地方都是要学习的,要知道他们运作的门道,有诸多的影响因素。一个国家要有准则,有道义,要考虑,要相信科学,要有诚信,要有人类共同利益的概念,再谈可持续发展。国别的理念和价值观也是在变化的,我们变化得很快,从人均200美元到人均8000美元的国家,我们的立场,我们的观点,角度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别利益有发展的问题,竞争力的问题,话语权,责任,权利,还有政治互信很重要。政治互信在气侯领域遭遇了一次外交上的挫折,就是哥本哈根。政治互信是很脆弱的东西,中美后来的合作有一个经验,也适用于现在的中美,就是互信是可以培育的。最后中美就做到了互相交底,战略意图越来越透明,分歧就是分歧,但是越来越透明,乃至于我们有巨大分歧的情况下,达成了妥协,达成了政治上的共识,这些都是值得吸取的经验,在未来做全球治理,做周边关系。
另外还涉及到决策者的层次,有时候元首层次说的话和工作层次说的话又不一样,国别的战略和行动的推进又不一样,中国有十三五规划,气侯变化的国家战略,美国也有。还有领导人直接的关系和属地程度,一起弹弹钢琴,打打猎,散散步很重要。
有时候非正式的渠道,当时高层马上意识到这可能是中美之间的一个机会,是中美一盘棋中的一个棋子,但是我们没有这个意识,只是工作层说这个事情本身,政治家在大的政治格局中就开始玩,最后我都没有想到两国元首签了三次,就是这个事情。
最早我们就是从这里开始。接下来又来了,他在总统科技办公室工作,说这回有点信了,想一起谈谈两国的减排目标,我说这个事情哪能谈呢?我说这个不太可能吧,我说你回去跟你们总统说说,我们谈一点中美打算在这方面合作的,或者是为了在巴黎合作而合作,反正不要直截了当的说目标,这个事情的困难太大。总统的决心已定,我们没办法改变总统的决定,那吨饭是在清华吃的,因为我们一起在分管学院那里搞了一个学术研讨会,都是学者,底下的都是暗度陈仓,回去又赶紧写报告,说他们要谈这个事情。而且再过一个多星期他们的代表团就要过来,国内的决策要请示领导,专家要提论证意见,多少个不眠之夜。逐渐逐渐的就开始巨大的差距在弥合,完了就是怎么谈?先搞专家对话,也就是所谓的1.5和2委对话,包括看芝加哥公牛队的比赛,吃牛排馆的牛肉,第一次就是跑去芝加哥对话,到华盛顿对话,在北京对话,有无数个对话。后来跑得太累了,时间也排不开,就视频,网络好用。微信都用过,经过这么多对话,基本上双方至少把对方的想法摸透了,然后开始到部长级的对话。谢主任和他们的克里的气侯特使谈,谈着谈着半年就过去了,突然发现apace的会议要开,奥巴马要来,两国的东西必须在这个期间签。是主席工程。这个时候双方都是总统亲自,元首亲自来遥控。
我后来听说这个发改委那一年有一个政绩,就是我们得到了国务院领导、中央领导的多少多少条批示,这个批示里面百分之几十都是关于气侯变化的,就是为这个事儿。
到最后剩一个分歧是拿不下的,是关于2030年前后达峰,美方坚持要到8亿,中国是左右,就谈不下来。还有一个分歧点是关于供区原则,这是政治上的分歧,美国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中国的必须得有,没有的话我无颜见发展中国家的兄弟,而且中国也是这个观点。这个没法弥合,这是意识形态的分歧。
最后这个问题是由我们的司长,他非常智慧,提出一个建议。既然你不接受这个,后面还加了一句话,你不能歪曲了我的意思,没有这个frees,单放一个共区原则我是不能接受的,用的是No way,都急了。最后袖子都挽起来了,一夜一夜的谈,也没有时间洗澡,24小时,48小时,那边的元首等着呢,中办一会来电话,你们谈得怎么样了,都属于半昏迷状态。
这时候司长说把这句话的前面加一个逗号,他们就说我们琢磨琢磨,就到边上讨论,一会儿又打电话,加了一个逗号就把后面的意思隔开了,英语里面就可以有不同的解释,我们只能谈下不同的解释权,但是现在看来一定要拿下是不可能了。美方又回来说还是很不满意,但是我们可以考虑,但是我们必须向白宫报告,最后第二天早上来了,说白宫批准了,可以加个逗号。这是谈了几年谈不下来的事儿,就是因为一个逗号。
不要小看这个逗号,这个话就变成了几个星期之后利玛大会的一个定音,利玛大会是巴黎大会的前边一个大会,那届大会要破例,巴黎大会就悬了。当时的政治任务是巴黎大会必须得成,翻车的是中国控制不了的,是190多个国家谈,非洲兄弟不干了,最后中美两国很秘密的到了一个小咖啡馆里,美方说要跟谢主任喝杯咖啡,谢主任点的是茶,美方点咖啡,我买单,到现在都没给报销。外事财务规定说这个就是自己的零花钱里面解决,谈的就是这个逗号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咱们能不能用这个去说服其他的缔约方,偷偷的做工作,不敢公开的。中国公开的做工作,印度那些发展中国家说你这个叛徒,跟美国人折腾到一块儿,但是确实是跟美国人折腾到一块儿,不折腾一块儿就搞不成这个事情。我们就悄悄的做工作,先到LMDC做工作,一个个的,给我的感觉就像杨子荣进了威武厅的感觉,一个个都怀疑,他们其实怀疑中美在背后在干什么,跟公约秘书处干什么,我们是干了什么,不干什么哪有今天的巴黎协定。
但是我们是苏司长亲自去谈,这是我非常佩服的,国际上绝对是绝才,跟人家沟通,说我们现在看看什么重,什么轻,必须要的是什么。说我的供需原则,咱们要去说服他们,这是最后的机会,有没有巴黎协定,还有很多很激进的发展中国家不接受这个东西。我们就要做他们的工作,苦口婆心。我为此还给某国家的代表,代表中国美的的电饭锅,这种工作都做过,变成铁哥们,至少不要驳我的面子。这部分人做通了工作之后,整个144多个代表团大体上就接受了。
美国拿着这个东西回到他的集团做工作,一开始也有反对意见,但是如果说美国接受,他是领头羊,基本上那些都接受了。这样就把两大集团弥合了,挽救了利玛大会。中美联合公报就用原词,加上逗号的这个原词搬过来,全世界接受。
所以看中美在这里的合作,在全球治理的运作过程中的合作是起了关键作用的。以至于后来到了巴黎这个环节,最后的环节,还加上法国是主席国,最后他的外长到了我们面前,说谢主任您打算怎么说?我就把它写成标准的英文和法文,您写中文。六个联合国的语言就有三国了,其他的让译员去弄,但是中、发、英文咱们自己搞好。最后几家撮合。
中美最后一个关注点是怎么解决的?这个工作层无论如何是拿不下来,这是两国元首在银台解决的,原计划9:30结束的,最后接近10:30才结束。外交部的同志跟我们讲是奥巴马直接提要求了,为了气侯这个会谈延长了40分钟。习主席把这个事情拿下,说服了奥巴马,但是加了一句话,“我们在2030年前后达峰,争取尽早达峰”,也是做了一个小妥协,但是奥巴马的压力是非常强劲的,说习主席必须接受我的意见,说如果我这个意见要是没有被采纳的话,我回去这个事情就算我签了,我们的团队意见也很大。说了很多理由,这个事情为两国总统多谈了40分钟,但是我们就用这个办法拿下。
有了中美的基调的东西,包括中法、中欧的基调的东西都拿下了。到了巴黎协定,12月份签的。前面的暑假,还发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当时就跟谢主任说11月初要访问,就谈气侯的议题,但是我们必须准备一个文件。谢主任回来之后,就说有几点意见,一定要写一个东西,在20天之内我们要回信。说我最近就准备休假了,休假回来就要看到这个稿子。我当时一楞,我说您休假了?我不休假?我盼了一年的假就黄了,我们有五个人,和气侯司的同事,一个暑假20天就是写这个稿子,写完了就跟他们的气侯大使和他的外长磋商这个稿子,到11月初领导人来北京。当时中方还想谈点贸易,谈点其他的议题,奥朗德说这次就谈气侯变化一件事,最后还做了一些修改。
这些铺垫最后成为巴黎协定的最坚实的、难啃的骨头,在这几个声明中解决了。欧洲人特别担心的是后面有没有这个机制,有没有重新更新目标的机会,这个我们也解决了。这样才得到了巴黎协定。
所以今年达沃斯的习主席的讲话说“巴黎协定来之不易”,我说最知道来之不易的就是我们,是真不容易。
但是我们有理论,发展路径,创新等等,但是你也得有实践,外交的实践,国际规则应用的实践,这样才能最后把这个事情搞定。应该说巴黎协定是一个比较好的反映了各方关切,也反映了我们的观点,当然现在还有很多未尽事宜要做。
也有一些启示:
一个是把握方向,坚持原则,坚持定理,有所作为。光荣孤立。光荣孤立不是我们要追求的结局,而且要尽量避免。为什么要孤立呢?但是你到了艰难的时刻,有时候要坐得住,你要别人都在跟你挑战的时候,你要一脸笑容,这个是需要胸襟的。
第二个是定位。
第三是大国外交。虽然是一国一票,有一个国家不同意,这个协定就不能达成。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当然我们也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互相尊重,但是不可否认,大国的外交,大国的合作在全球治理中的特定作用。
四是国家体量,实力,意志的影响,硬、软实力之间的转换、结合。硬实力转换成软实力还不是自动转化的。需要培养,需要学习,这些都是我们得到的启示。
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统筹,还有运作的艺术,还有一些外溢的效益。为什么我们这么重视气侯谈判的效果,因为您在这个领域中取得进展,取得地位的话,可能外溢到经济领域,安全领域、政治领域。所以现在注重全球治理,是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发展到今天,一个必然面临的局面,也必须是主动的学习和提高这方面的能力。因为我也深切的感到自身在体制上还是有弱点,当支撑我们在国际前沿去实现地位,话语权的时候,有时候就着急。盼着首都赶紧来电话,来指示啊,怎么过了一两天都没人理?有的时候就说我们的谈判代表都不知道,所以要协调,这些都是体制能力的问题。
不同部门的不同意见,这个部门出去这么说话,那个部门出去那么说话。
给大家看几个数,这三张图可以说明中国的地位,看中、印、美人均GDP的比较,80年到2015年,最上面的是美国,红的中国,蓝的是印度。也就是说在人均GDP上,中国和美国的距离在扩大,总量是在缩小。当然比印度又拉开了。也就是说中国从2000年以后,和印度的水平在拉开,跟美国人还没追上,还差很远。有新兴经济体,有发达国家,有最不发达国家,这就是定位。
这个是二氧化碳排放的比较,美国在2007年以后开始下降,中国在急剧上升。印度变化是稳中有升,并不大。这都能看出中国的地位,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时代的使命,从人均GDP,人均GNI,和人均二氧化碳的排放。这是中国比印度比美国,80年代,是1:14:64.6,2015年人均GDP是1:0.2:7.0,也就是人均GDP跟美国在缩短。人均GNI在1980年是1:1.3:61.0,2015年是1:0.2:7.1。我们面临着中等收入陷井,特殊性在于全球和局地的资源环境对增长动力的约束趋紧,还有中等收入人群占比持续上升,导致对环境舒适性、健康安全的需求上升,需求结构变化的动力增强。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你们要去北京的亲戚、朋友、同学,家里家家都会花三千块钱买一个空气净化器,这就是支付力。如果告诉他花三千块钱雾霾就没了,你让他花6千都花。但是 现在缺少这种社会机制,说保证让他花6千块钱雾霾没有,他觉得传递不过去。不现任你们,你们会不会腐败?会不会干了什么事儿?这种社会机制是需要建立的。
中国对策,中国自身的战略,人类利益共同体,这些我就不展开讲了。但是我再一次强调中国的定位,中国是发展中的大国,中国还是一个文明古国,中国更是一个在崛起中的大国。这个我们要自己有非常深切的认知,整个国民要有认知。中国的解决方案这些都不长谈了。
一个是排放达峰,要提前和加速。这个是有意义的,也是有动力的。现在的进程应该加快,而不是停滞、延缓。加速排放达峰意味着经济加速升级、转型,减少陷入中等收入陷井的宏观风险,为实现第二个百年梦想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
加速达峰意味着加速达标宏观经济要素效率竞争力,有利于形成长期繁荣的后晋。
意味着结构调整,是经济转型升级的助推器。而不是增长的绊脚石。
清洁高效能源技术,市场的实际发展和十三五目标实施的实际进程表明,加速达到峰,提高目标力度有很大的潜力,中国应当为提高NDC目标力度做好准备。
加速达到峰要求加速体制和政策乐得改革,驱动利益相关方加速行动。
这样一个准备提高力度,2030年提的是节省60%到65%,到时候能不能提到75%?超额完成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有更高的起点,难道还坚持2030年是6065的目标吗?难道不应该变成更大的减排力度吗?这些都是给我们提出的问题。当然还有加速达峰要求,体制和政策的改革。
加速达峰有技术路线图,我就不多说了,有边际成本曲线,这个是能源结构,这个是天然气的过渡是在这里,我从2015到2050年怎么过渡,底下的蓝颜色是非化石能源,中国包括大水电,还有核能都在这里,我们希望这里面是可再生能源为主。橙色是煤炭,2015年的时候占到了60%以上,到了2050年可能占了20%以下,从这样的状态过渡到这样的状态,中间把喇叭口缩短,主要是靠新化石能源,另外是天然气。到2030年达到这个程度,到2030年就不再投资了,从2030年到2050年还有20年,2030年投的资经过20年也够本了,也赚足了。这里面还酝酿着2050年左右和之后大规模的淘汰天然气,这是一个几十年的安排,大规模的替代煤炭。油也在缩小,将来滚动做长期情景的时候,现在电动车方兴未艾,有可能把油再往下压,但是这些都依赖于非化石能源迅速的上升。这个时候35年的战略愿景,就会被解释为5年计划,10年计划,解释为今天投资的特别是基础设施投资的建议,解释为技术研发和技术部署的建议。
这个是投资领域的分布,也不多讲。
这张图简单讲一下,在深圳谈判市场有额外的含义,有一个基本的建议,就是碳价的上升,总之是上升的,把减排的目标以及技术的部署和碳价格联系在一起,碳价格是依据实体产业的成本,以电力行业为例,电力行业从2015年到2050年之间的部署,这个是PV电池,太阳能板,这个是风电,他们的成本越来越低,现在风电的价格,太阳能的价格,公司投标都有到4毛钱的,在美国是7美分的都已经出现,7美分算下来是4毛多钱,已经很便宜了。煤电现在是2毛多到3毛,如果不断的把环境成本加上,他是往上走的。这些技术渴望在30年以前大规模的部署。之后再部署更先进的也更贵的技术,离岸的风电,太阳能发电,再往后的40、50年就是CCS。每一项技术的成本都是斜着往下走的,就是说成本在不断降低。
想想手机的价格,想想电脑的价格,就能够理解。我们把所有的技术变动的过程,成本的过程,时间的分布,以及市场价格的分布,建立起联系的话,我们就会形成一种概念。现在国家宣布要起动全国碳市场,我们想告诉那些长期的战略投资者应该往哪儿投,趋势在哪儿,可能会有波动,但是如果你的投资是管十年二十年的事儿,如果往基础设施里面投的话,那么大势所趋在哪里?这些都是中国回过头来怎么安排自己的事情,从谈判,从全球治理,在全球治理中的选择,以增长方式和发展路径创新作为中国参与全球气侯治理的国家学说,还在不懈的动员领导,动员媒体帮我们说。
刚刚结束的一带一路峰会,还把这一条建议给能源基金会的全球总裁,他原原本本的把这句话用英文念了一遍,很多报纸都报道了。政治上要坚持发展中大国的定位,这个没有错,但是增长方式和发展路径创新上要精准的定位为我们处于转型之中的中高收入新兴经济体。这句话在部委里面有分歧,几个月前的一个会议上,这是内部的一个讲话。当时几个部委的人就出来了,说邹教授你的提法和我们的标准提法不太一样。我说如果这个会议上还提一样的,就没有增加值了。但是我们可能需要一个精准的定位,除了泛泛的定位之外。对于供需原则要做出与时俱进的解读,一个要坚持还要坚持,但是要并重的强调区别,肯定是有区别的,但是共同的责任,过去我们是一带而过。现在可能要非常认真的想,非常认真的做,这个时候我再说有区别的责任,才会更有依据,才更符合实际的进程。
还有是要积极发挥大国的引领作用和示范作用,加强国际合作。
重在通过推进本国的低碳发展实践赢得全球的竞争力和话语权,以最大的努力达到最大的力度。
现在中国有没有这个话语权,有没有引领作用?有一次我说这个“引领”中国人能听懂,能不能把英文的语境扭过来?有很多词外国人听不懂,所以中外之间的语言差距要怎么贯通,这是一个沟通的问题,而且也是自己做的问题。
你看中国的风力,大量的气光,美国的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量是最领先的,装机我们是多得多。但是装了不用。
总而言之,我就说到这里,有什么问题讨论讨论。
李津逵:传说中时间最短,牵涉的国家最多签署的一个气侯协定,他的背后原来是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很可能中国谈判的代表,你在京都,在联合国的框架都要付出得多得多的努力,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直在穿越,邹老师又是一个经济学家,又是一个环境学家,又变成了一个外交家,所有的这些我原来都没有听说过。因为我的印象中还是他跟我讲课的那个时代,在清华的足球场上奔跑的马拉多那。
确实是时间有点长,谁如果有点累,就不安排时间单独茶歇了。
现在提问题。
范志明:真的是非常享受,我了解这个事情是很长的,从最早的很艰难的哥本哈根到现在,但是一直是一个纯粹的局外人。看了这么大量的工作以后,有一个疑问。谢振华一直说他有王石和很多企业家的朋友,我想知道在这样的国际气侯领域中,中国除了政府的决策之外,其他人的,包括企业家的决策,包括公益组织的,NGO组织担负的组织是什么样的?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想知道在类似于像戈尔这种美国为代表的公益组织,又在这个里面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邹骥:很好也很深刻的问题。
观察到的表象,中国企业起了什么作用?在决策过程中几乎没有作用。但是在舆论、话语的环境上也是有作用的,他的作用是这么体现的,一个是每年去联合国气侯大会有一个中国角,王石就亲自资助过这个中国角,而且每次办企业家环节的时候,像王石,马云,潘石屹都去过,在那里呼吁要保护环境等等等等。但是这个是非常浅层面的。
要说中国的企业家很复杂,国有企业的领导人算不算企业家?也算。假如说真正成为目标了,又要注意,煤电,几百万煤矿工人,要失业,要悠着点,这个目标要留有余地,所以这些都来了。当然是要认真考虑的,他们的意见往往是通过工信部,通过有关的主管工业的部门体现出来了,有时候去到能源局,原来的部委会商的时候,不同的考虑的角度就出来了,他们的意见是这么体现出来的。
但是比较国际的跨国公司,500强的那些企业,我们的社会治理结构是不一样的,他们的工会力量太强大了,他们对选举有影响,他们的相关产业所在的洲有影响,这是在美国的情况。欧洲的情况,默克尔是多么激进的环保主义者,他当过环保部长。但是在钢铁联合会面前,在煤炭协会面前,他也不得不让三分。包括他设置了很多宽限的条款,在国内减排的时候,最后有一个,如果德国的钢铁企业如果面临着跟中国的钢铁企业竞争的时候,我是由于碳失去了我的价格优势,那么我可以得到豁免。有一个特殊条款,所以说他的企业会游说,而且到了联合国现场,有两个办公室是NGO的,就到了你的第二个问题,NGO非政府组织,一个叫bingo,一个叫yingo。有一个著名的组织叫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组织了全球500家的在那里,他们在那里发自己的演讲,自己的小报,自己的宣传品,说老实话,我没少吃他们的饭。因为谈判忙啊,说饭总得吃吧,出来跟我们说两句吧,就帮你买点饭,你就吃一吨。但是我们没有要求说利益冲突,因为他们说这也是听取外界声音的一个机会,他们就利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什么比尔盖茨去见总书记啊,克强总理啊,6月初在北京开的清洁能源会,中国马云都参加了,这些都是企业家在那里发挥作用,他说我得创新,我们先投10亿美元,政府要答应,你们的研发基金,清洁能源的研发基金要增加一倍,这也是一面推的力量。很活跃。
相比较而言中国的企业不够活跃,有体制的因素,能力的因素。
但是我又看到了一批特殊的企业家在崛起,比如说王石,潘石屹,马云,他们都很热心环保事业,但是跟那些所谓500强的比起来,我们总体上还是企业做得不够。
NGO,中国的NGO整体是弱的,但是已经加入到了一个CAN,那里面已经有中国本土的NGO参与了,也经常跟我们交流。但是NGO有一个更深刻的内容,就是我们的社会结构不一样。在西方社会的NGO是非常强大的,我们甚至于形象的讲是三分天下有其一。政府、企业、公民社会。有很多智库是在这里的,他有经济基础,就是捐款,它的税制,从制度上保证了有一大笔钱必须捐出去,捐给各种基金会,包括能源基金会都拿到了这种捐款,这种捐款拿出来要花出去,就发给NGO,大学,智库,这是一大笔,先不说慈善家的慷慨和高尚情操,就说制度保证了一定会有这么一笔钱。欧洲不是这样的情况,欧洲的NGO也有私人捐,大部分是来自于公共财政,欧盟委员会,政府有一笔钱要给NGO。
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里面有多少钱呢?先不说给NGO,给事业单位,综合发展研究院是NGO,法律性质上是NGO,但是大部分的中国科协等等,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其实这样的钱还是比较少的。但是中国面临的一个挑战和问题,你在面向国际社会的时候,我们已经习惯于政府间的对话和博弈,非常娴熟,也非常的power,跟企业,跟外资企业,跨国公司,对外开放,招商引资,企业家一来领导人都得去见,上至总书记,总理,部长,下至省长,市长,肯定要见的。比尔盖茨来,他见国际的正国级领导人很容易,一般都要安排见。怎么我想见就见不着,我只能坐在人海之中,在电视里面见,这个是我们很重视的。
但是他们的NGO有一个我们对西方社会更深刻理解的问题,他的NGO对他的选举,对它的思想的产生,对他政治的运作,都是有重大影响的。他们在整个社会主流舆论里面是占有重要地位的。我们一做白宫的工作,国务卿的工作,实际上美国的原创还是在大学,用一些大学的思想家,一些原创的观点。但是直接消费者是谁?那些新闻记者是不会读那些书,也不会读哈弗的某个教授的《人民的冲突》等等,那些智库的人,或者是基金会,他们都是精英,他们消化了就产生很多观点,中美关系,气侯变化,北极问题,他们还在设置议程,说现在该谈谈北极问题了,现在该谈谈超核问题了,恐怖主义问题了,网络按照问题了,他们提出议程,各种观点,各种方案。这些东西去了哪儿?没有直接去白宫,当然你也可以直接给白宫写。但是一般的流程是去了媒体,去了各种各样的媒体。这个媒体又把它加工成一个可以是情绪化的,可以是大众化的,反正上上下下都知道了,中国偷美国的技术,中国倾销,中国把我们的就业机会拿走了,矿工啊,协会啊,都变成了政治观点,在国会里面折腾。这些进入白宫的人,他们当年是在智库里面呆的,他在这个环境中就跳不出这个氛围。从这里再进入政府,进入议会。他的智库后边的所谓的NGO,智库本身大量就是很多的NGO,这就是他们的作用。
这是他们的结构,跟我们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根本不是一回事,但是我们现在要跟他互动,是不是要有效的解决利益共同体的问题,我们要融合,要一起共筑新的世界秩序,这个时候我们中国的经济体和社会,和国家,怎么去跟他们对接。我们还要坚持理论自信,文化自信等等四个自信,国企要设党委,党委要和董事会有某种关系,还是大学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还是大家都来两学一做?学什么?当然肯定要学,他们也学,学得很细致,每次一有新的讲话,驻华使馆的政治方案,就要请你吃饭了,就是有重要的文件出来了,十三五啊,就要我去谈一谈这一段是什么意思。我说我还没来得及看呢。他们学得很认真,两学一做,这些人做得最好,外国智库做得最好。因为专家讨论说什么都行啊,能源局啊,十三五规划啊,发改委一出来,怎么就变成了11亿?也有人说13亿的,也有人说9亿稳定,8亿的也有,一下变成了11亿,我说我还得学习。
这是我们要更深入思考的问题,在这样两种不同的体系下,咱们一出去,习主席在美国访问,一路美国很多智库,很多议员想见习主席,这怎么能见?
但是反过来看美国人到中国来,大人小孩的能见的就见,能吃吨饭的就吃,能多聊一聊就多聊一聊。习主席在那边也召开座谈会,企业家座谈会,侨界的座谈会都有,但是跟他们的路子还是不太一样。这些都值得思考,我没有答案,你提的NGO的问题,企业的问题,我是把这个问题的思考框架放到一个社会结构差异和怎么发生关系的问题上来。
提问:非常感谢今天做了这么精采的报告,让我们很敬佩,您的整个谈判过程,中国在气侯治理方面做出的贡献。
您刚才讲的过程中提到了在发达国家,人均GDP达到2.5万美元的时候就达峰,中国可能是1.4万美元达峰。深圳去年的人均GDP已经是2.5到2.6万了,这个是按照常住人口公布的,如果是按照管理人口可能还要低很多,大概是1.1万美元。现在的管理人口如果是按照1500万来算。如果是这样,如果按照户籍人口是已经达到了峰值,但是我们目前做的研究,以及城市温室气体清单的编制,已经有十年的数据,从现在来看,承诺是2020年达峰,当时也做了一个研究,2020年左右会达峰。但是从人均GDP的规律来讲深圳应该达峰了,但是现在仍然看不到,达峰的路径也在研究。如果是按照数据来讲,现在应该达峰了,但是目前没有达峰,问题在哪里?
第二个问题,您刚才提到的国外达峰的时间和人均GDP,这一块是中国人自己研究的结果?还是发达国家自己发展轨迹中的结论?
邹骥:第一个问题后面还有专门课题,这个统计口径让结果有很大变化。特别是中国的预算人口老是有常住人口,管理人口,口径不一样。现在也只能按照官方的统计这么算,这个之间能不能比,我们的人均GDP和他们的人均GDP是不是说的一个东西,他说的也有争论,法兰克福的人均GDP一算很低,比法兰克福中间的低很多,有人说GDP都在法兰克福中心城市产生的,但是怎么一算,中心城市没多少呢?都跑到周围去了?因为大家住在周围,按居住地一统计,交税的又不一样了。这种统计一直是有差别的。但是作为一个大的经济体,这种误差又小了一点。
所以首先划的经济体都是大经济体,小的根本没办法往上写。比如说美国3亿多人,英国5千多亿人,德国8千万,法国是五六千万人,中国是快14亿,用大规模的经济体来比,可能会稍微好一些。深圳的1500万人还小了点,当然深圳其实低碳的步伐并不快,就是用了这个指标,人均GDP常住人口是2.6万,但是还没有达峰。因为这个不是定律,只是一种统计观察,这些国家大体是在这里。找到一个数量级,先测量深圳在哪儿,至少深圳还没有比发达国家更先进。您说是2.6也好,2.8也好,2.5也好,按说应该达峰了。但是其实这个日子也差不多了,是2020和2022年,这个在历史的长河中基本上是一样的。如果2022年达峰和2020年其实没什么区别,基本上还是落在2.5万美金左右。
但是在全国的范围内看,确实也是模型模拟的,我说的1.4也有可能是1.6万,但是肯定不可能过2万,是1万多,模型是这种感觉,会有一个误差带,这是其一。先从测量上看出深圳是什么时候达的峰,但是一个基本的结论,就是深圳达峰的步伐并不快,而且并不像全国那样说要在一万多的时候就达峰。这是第一个结论。
为什么还没有达峰?
大体上可以从几个渠道上找原因,一个是能源结构,深圳当年弄了天然气,肯定比北方的要好很多。核能是不是也不少?因为深圳有大亚湾,如果电的调度算南方电网的排放因子,可能会冲淡了。如果要有更局域的电网,假如说香港列入深圳,一下子就可以把我们的碳下来很多。另外是可再生能源占比还比较低。
还有天然气,刚才说比北方好,但是跟欧洲、北美比,我们的占比还是不够高。能源结构上。
能效上,可能得检查检查交通,还有一些制造业,尽管跟全国比深圳的制造业先进很多。连欧盟都没有看到峰值,如果欧盟都压不住,中国大量人口的交通需求还是很低的,反过来一般经济发展到成熟阶段,特别是后工业阶段交通和建筑是主要的排放源,在欧美在三分之二以上。中国未来的后峰值的研究重点是在交通、建筑,以及基于消费的经济活动。国际上现在对中国的要求是必须迅速下降,不迅速下降,那两个目标是实现不了的。但是这个是很难的。我们也看到一些机会,比如说交通第一步真的实现了电动汽车的迅速扩展,而不是私人汽油车,包括运货的大负荷的运输设备,更多的用电动机车,大型的柴油车也用电动的替代,这个是一个新的路径。效率首先是要比汽油车高。
其次要改变发电的结构,如果他们还用的是煤电,这个碳还是很高。如果是非化石能源在发电中的占比或者是低密度的能源多一些,这个电动汽车就有可能,至少不会到三分之一的占比。
还有建筑,中国是有希望的。现在推广65%的节能标准,原来是55%,现在新建的小区要求65,这还是第一步。除了技术的标准之外,居民住户使用的习惯,比如说在北京是夏天愿意开窗户,南北通透,当然特别热的时候没办法,只能空调。西方国家的窗户是密封的,他们没有开窗户通风的习惯,在制冷供热的问题上就有大量的能耗。另外他们的习惯是从早到晚的空调得开着,6月份还在开冷气,天气凉嗖嗖的,可是一到了西方人的习惯就变了,多冷的天也要穿个T恤衫,那个能耗确实是比较大的。更多的还取决于基础设施,供热系统,制冷系统,一些根本的技术。
中国的建筑节能每平米消耗的能源数是要远远低于欧美每平米的数,另外是我们住房的面积,这是一个大的课题。将来中国人均面积,有人说现在已经超过了日本,超过香港,但是装备率很低,当装备率上来的时候,特别是那些城镇化的人,从村里到镇里,从镇里到县城,从县城到省城,当然大部分人还基层,就是县、镇,还有地级市,现在去库存是要去这些库存,真把库存去掉的话,其实那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可以用起来的房子,空调得开起来,供暖得供起来,电器得用上。那个时候对我们的冲击率是一个考验,而他们的用电方式是怎样的?现在想建议大量的,甚至是长江流域地区的供热,他们都是有供暖需求的,这个时候能不能用地源热泵,加一些电,而不直接用电取暖,更不能用煤取暖。甚至不用天然气,当然也有一部分用分布式的冷热电连供的天然气装备,都比你用传统的煤供热的系统等等好。
如果我们实现了这些技术之后,中国的建筑能耗有可能比西方国家要低。但是现在我们在算这个帐。深圳用空调的时间比较长,可能有六个月,这个得算一算。
总之如果我们在建筑、交通上和基于消费的经济活动上,如果把能耗降下来的话,是有可能实现创新的,我们看到了技术前景。
关于没有提前达峰我们还要看具体的。
说起来很自豪,真正做到是很艰难的。
嘉宾:很担心国家2030年达峰,人均GDP1.4,深圳按照现在在全国的发展进程和水平、阶段来将,应该是后工业化时代,和发达国家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很相似了,因为我们的工业时代已经是在往下走了,但是我们还没有达峰。应该说深圳是走在前面的,目前都没有看到峰值。
刘宇:能源革命是应对气侯变化的核心问题,您最后也谈到了未来到2050年,可再生能源和非化石能源占比要占非常高的比重,从实际情况来看,风电、水电、核电,光谱发电,2016年没有用完的电相当于是一个厂发的电,这是巨大的浪费。对于已经装机了,也没有发电的,这是一个损失。
关于补贴也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企业投资了,但是按照政策也拿不到补贴,这也对整个社会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资源浪费。如果按照您的设想,2050年新能源,非化石能源占比要达到那么高的目标,但是现实中又有巨大的问题,更不要说深层次的问题,体制的问题, 现在的电力体制和能源体制是以传统的化石能源来设置的,垃圾电,长期来看这个问题也是需要解决的。您有什么建议推动解决这些问题,让新能源或者是可再生能源在宁愿结构中占比比现在的更高,如何推动?
邹骥:刚才说气侯问题是长的、大的尺度,2050年,比喻成万里长征。但是我们得知道怎么走,往哪儿走,先提供一个方向,一个愿景,坚定这个方向。如果连方向都不明确的话,有时候改革也好,做的很多事情也好,可能就是在原地转圈,原地踏步。现在是明确方向的问题。
明确了方向之后,确实是万里长征要始于足下,比如说要变成一个20年的计划,然后10年的计划,然后5年计划,然后年度计划。要协调起来,一致起来。年度和5年的事情,如果在基础路线图上大体方向上、概念上取得了共识之后,就得优先的部署,部署上就有技术上的困难,比如说电网的人,特别是国网的人,就把垃圾电源,本身这个话就带有歧视性。
无论世界、国家还是人民的利益,是要求你们做出变革的。你不能上来就说可再生能源是垃圾的电,态度、观念上就要转变。我记得在今年3月份中国发展论坛上,当时安排我和利卡斯顿与几个公司界的老总对话,那几个都是国电的老总、VP的老总。当时我就说了一句话:搞煤和煤电的,企业最终不是说发了多少电,多少煤,是问有多少利润。把投资做一下扭转,今天要保持稳定,该发多少煤电,先保持稳定的做着,但是在新的投资上就别再往这个里面投了,能不能想办法往一些新的技术,新的能源上投。这是对企业提的要求,将来要指望那个来挣钱,变成你的盈利点,但是跟企业说这个事儿还不够,也不公平。就得跟国家说,跟能源局,跟税务总局说,人家企业要往非化石能源领域投,政策上有没有优惠,免一点税啊,当然给补贴现在也不太成功,但是免税是可以考虑的。另外在项目的审批上,土地的供给上,给一些优惠,人才等等,中央地方政府有一些具体的措施引导,扶持。
另外是在技术上有一些措施要不断的推进,落实,有时候不是钱的事儿,有时候就是利益的事儿。比如说风电,太阳能这些事后有可能做到30%以上吗?中国现在也就是不到20%,重要那么牛,电力行业都要做全球互联网了,你说跟德国的10%的差距,我问你差距是怎么来的?当然有很多特殊的情况,中国的分布不均匀,大量的都在西北地区,东北林区,电网上是有缺陷的,那就补短板啊。电网的建设上疏通,把三北的光伏和风电疏过来也是一个技术。
另外是抽水蓄能啊,等等在有条件的地方就可以做,在水库就做起来,这也是一种补救的措施和提高稳定的措施。
另外是电动车系统,科学概念早就提了,如果电动车迅速发展的话,会变成一个集体的储存设备,千家万户的电动车的电池,晚上,在峰谷的时候,把可再生能源的电存起来,白天的时候再发出去,这种技术设想是可以往里做啊,投资啊。
现在主要障碍不是技术,当上网率达到20%的时候,没有主要的技术障碍。可能投资上有障碍,到30%的时候可能有技术障碍。当下弥补这10%,弥补完10%的时候又有新的10%的机会,但是我认为主要是利益的障碍。利益的障碍就是既得利益者,现在谁上网谁赚钱,谁批煤电项目谁赚钱,因为审批权在地方政府,都愿意批,因为稳定,也占据市场。上网的煤电又便宜,成本又便宜,也不用从利润背他的成本,但是煤电的便宜是因为国家没有收污染费。能源法反而有国家,最近听说有一个NGO,听说高法的同志告诉我,说已经有NGO在起诉国网,《能源法》规定要足额的上可再生能源,有《可再生能源法》,你为什么不上?你违法了。在做公益起诉。当然中国的法治社会还是一个口号,但是有这种实践旧好。国网就要回答,无非是煤电的老总跟我叫苦啊,我没法调度啊,就得调啊,如果再不调,还要不要当国企的老总了?中组部难道还让他们继续当国企老总吗?这个事情按道理说到底,我觉得问题在这里。
这些事情都应该做。
李津逵:今天我们已经经过了三个半小时,但是我们重新的思考了国家的定位,他是从一个发展中国家已经走到了一个新兴的经济体,而且是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可以起桥梁作用的巨大的存在,我们的路径不再是原来的那个路径,要走一个增长方式的创新或者是发展方式的创新,而且在达峰的问题上就要明确的提出方向,有了方向才能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没有方向的话就是乱走了。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看起来走到世界看清楚中国,再看清楚中国,我们的未来就是一个治理,就是十八大说的,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如果没有这件事情,靠科学家,靠外交家在那里,真的是很难实现2022、2030。
热烈掌声感谢邹教授。谢谢你让我们更加看清了世界,看清了中国,看清了深圳,看清了我们身上的使命,而且今天的话题就是6月2日银湖沙龙的话题,我们将在王国维先生90年的纪念日的那天做一次关于深圳未来一定是双语城市才能承担使命的猜想,主讲人是原典英语的徐火晖老师。
谢谢大家的光临,谢谢邹教授。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