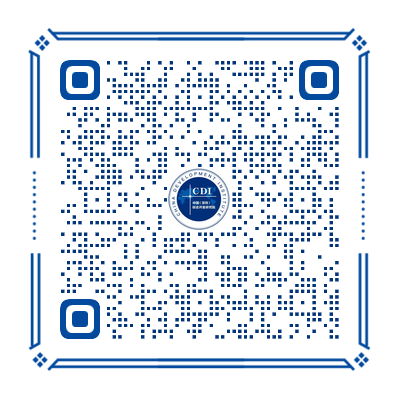明亮:社会学视野下的农村教育
时间:2011-08-21 08:52
在“广东省和平县首届中小学校长论坛”上的发言
2011年8月21日
一、社会学视野下的“城乡”
与目前社会主流惯用的以“城市化”来描述当今中国的经济社会变迁过程有所不同,在中国社会学的传统中,尤其是以费孝通先生为代表的一批社会学家始终慎用“城市化”的概念,而坚持以“城乡关系”作为探讨城市与农村发展问题的基础。这并不是否定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民进入城市、从事非农业生产并逐步转变为市民的一般性潮流和趋势,而是在中国现代化的特定语境下需要坚守一种理念——即城市与农村之间仅仅是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差别,并不存在价值层面的优劣。城市面临现代化的问题,农村同样面临现代化的问题,“城市化”的概念容易给人们造成一种错觉和混淆,即我们的发展路径是偏向“城市”的单一、线性的,方向不具有可逆性,今后大量农村地区会逐步演化为城市。在社会一般性的想象中,人们也习惯性的将城市冠以“现代”、“先进”、“繁荣”、“富裕”等描述词汇,而与之相对,“传统”、“落后”、“贫困”、“愚昧”则成了定义农村的各种标签。
其实在社会学的视野中,城市和农村分属两个既有关联但又截然不同的社会系统,具有各自特殊的社会关系网络、组织形态、制度规范等,各自遵循内在的规律和原则完成日常运作,只要外部性因素引入得当,都能够产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变迁动力,并实现预期的效果。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城市可以凭借区位条件和发展基础,在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下,迅速完成各类生产要素的集聚,创造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但我们也发现,在现实中传统农村地区和乡土社会依然能够创造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的奇迹。
案例1、珠江西岸的顺德:传统农业地区孕育出的百强县
案例2、大山深处的巫溪:重庆社会建设的高地
上述两个案例告诉我们:一是,传统农业地区同样能够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结合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形成支撑现代工业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实现经济的起步和腾飞。二是,虽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也具有相对独立性。大山深处的贫困山区依然能够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在短时间内在社会建设方面形成亮点,屡创佳绩。
这其实也提醒我们,尽管目前和平县的经济社会发展还相对滞后,但只要把握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并结合我们和平县自身特点,选择一个合适的突破口,同样能够创造不俗的业绩。我们这几年在农村教育方面的探索同样也验证了这一点。虽然经济发展水平是教育发展的重要基础,但两者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经济总量小并不意味着教育水平落后。
二、社会学视野下的“教育”
尽管上述案例中提到的两个地方在区位条件、发展基础、文化传统等方面也相差甚远,但它们之所以能够在某一方面取得成功,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充分重视“人”在经济社会活动中的重要作用,而“人”的培养归根结底靠教育。这里提到的教育不仅是狭义的学校教育,而是指的一个更加综合全面的社会性网络和氛围。
社会学往往从“人”的社会化和人与社会的关系角度认识和理解教育。与经济学将“人”定义为生产要素中的“人力资源”有所不同,社会学认为,人的社会化过程中不仅需要知识技能的培训,更为重要的是“人格”的培养。在这方面,我国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一直倡导“教育的目的是人格培养”的理念。他认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教育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每个人的人格培养。他还特意强调,“健全的人格,是要去假我以成真我,去偏蔽之我以成通达之我,去私我、小我以成公我、大我”。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教育的本质不仅在于知识的传播和普及,更是一种视野建立和感悟形成的过程。
在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潘光旦先生在教育理念上提出了颇具洞见的“位育”思想。所谓“位育”取自《中庸》,意为“安其所,遂其生”。主要是说教育作为一种人适应社会的制度安排,应该与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等相互协调配合,它们之间应该相互影响、共同演化。
这些观点和理念在目前国内教育尤其是农村教育中显得尤为重要。在外向型经济和市场机制的双重作用下,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城打工,农村社会出现大量留守儿童。乡村社会结构的变化使得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模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家庭和社会教育的缺位使得一方面农村社会的整合度呈现下降趋势,而另一方面也给学校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缺少父母关爱和对未来充满不确定的状态下,针对留守儿童,学校不仅需要传递知识文化,更要注重对学生人格的熏陶和培养。只有这样才能帮助孩子在内心深处建立自信,更加从容地面对今后的竞争和挑战。最近几年,由和平县人民政府、和平县教育局、深圳好人好事发展中心联手开展的“深圳和平.和平之光”公益教育计划,其中涉及的一系列活动其实都是在践行上述的某些理念。另外,和平县倡导的“文化育人”教育理念也与潘光旦先生的“位育”思想不谋而合,和平的教育应该从其历史、文化、环境中汲取营养和力量,只有更贴近现实问题和需求的农村教育才能使乡村社会的价值传统和精神传承得以延续。
三、社会学视野下的“文化育人”
虽然文化是一个内涵范畴极其丰富的概念,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但社会学却喜欢在较为“中观”和相对具体的层面加以探讨。如果以文化作为一种切入教育的手段和实施教育内容,那么作为一套这样的系统性制度安排,需要以某种组织化方式和相应的机制保障加以落实,才能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案例3、“久牵”:张轶超个人理想的终结?
张轶超曾是上海复旦大学的一名毕业生,因为机缘巧合接触到在上海的外来工及其子女,后来创建上海“久牵青少年活动中心”,主要为在上海的外来工子女提供免费的声乐及其它美育教育。虽然“久牵”自创办以来为上百名外来工子弟提供了服务,但无论张轶超还是机构本身并没有找到较好的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和模式。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教育是社会性的公共品,不能仅靠个人的虔诚理念和不求回报地付出来实现,需要建立一种行之有效的社会机制才能提供较为充足的供给。
案例4、“真爱梦想”:好人如何才能办好事?
而与张轶超的个体努力有所不同,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是一个由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的专业管理人员发起与运营的公益组织,并在全国许多地方建立了自己专业化的志愿者服务团队。这一组织同样在致力于改善中国的教育不公,希望通过系统化的公益产品和服务提供,使无论是偏远乡村的孩子,还是城市农民工的子女,都能够基于自我意识的觉醒,探索更广阔的世界和更多的人生可能性。
“真爱梦想”的实践项目之所以能够顺利的在全国推行和复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她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和行之有效的管理及运营模式。比如,建立专业化的顾问团队和管理团队、形成独特的运营策略和监管策略等。这也说明,即便是公益项目,同样可以借助市场的某些原则和规范进行操作实施。
和平县正在大力推动“文化育人”工作,这是一个大胆而有益的教育探索,但需要将良好的教育理念与有效的落实方式加以统筹考虑。在这方面上述两个案例也许能给我们一点启示。
最后希望以张轶超非常喜欢的一段诗做结,主要想提醒大家,也切莫陷入“制度陷阱”,毕竟教育不是冰冷的课本,她更是一种人心的交流和感悟的启蒙。
美国诗人希尔弗斯坦的《总得有人去》:
“总得有人去擦亮星星,他们看起来有些昏暗,总得有人去擦亮星星,八哥、海鸥和老鹰都在抱怨,那些星星已经老旧而锈蚀,想换新的我们买不起,所以请准备好你的抹布,和你的打蜡罐,总得有人去擦亮星星”。

明亮研究员在论坛上做主题发言

明亮研究员在论坛上做主题发言

城市化所曾真所长进行论坛点评和互动
(0)